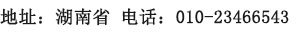我能想起的一朵小白花
在下雨,只有寂静,只有这雨制造的噪音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。走在早春的长涧河边,在雨中,这时的灵*——已被野地里的死马摸索着夺走——在下雨,昏昏欲睡的天空。我的本质?它已被我取消,我只是在想那 一片战火燃烧过的废墟,半掩在野地*和紫堇花丛,驾驭长毂战车的烈马死了:箭羽穿透前胸,左前腿粉碎,压在膝盖下——雨是如此的宁静,仿佛它也将穿透马的胸膛,而不是诞生于云朵——好像不是为了下雨,只是为了变成安抚马匹的一阵哭泣。远远地,我将看见纷乱啄食的乌鸦自风中飘升,面对一匹马的死亡,我还要过去向它告别——眼睛早已成了黑漆漆的空洞,这眼眶更容易看见黑暗中的虚无与永恒。在低语中,变得模糊的一切:这 是乌鸦干的。可惜才两岁大。还下雨,一切都不发光,包括黑暗的纯正和这纯种马。没有乌鸦的飞翔,我将感觉不到天空的存在。还在下雨,遥远,不确定,我不能够能靠近:它开始散发甜蜜的恶臭。该死的战车在我们疾驰而过时被四下溅射的泥浆裹住——我看见它,将会向它吐口水,眼中满是鄙夷与傲慢,像个贵妇。——那些确定的事物,没准也是个谎言。秃鹰在盘旋,围绕一个中心,它们在空中旋舞多么漂亮,可这并不重要,现在我知道,一切都是虚幻,是虚构,是梦,包括这逼近的死亡。还在下雨,除了这雨,什么都不能让我激动。而在这命运旋转不停的“咯吱作响”的车轮之上,我还将看见秃鹰盘旋,聚精会神,朝着马匹的心脏俯冲——永恒不变的中心——翅膀闪耀,闪耀。在车轮之上,我并不是此时此刻我正在观察秃鹰的推搡与争斗的那么一个我。我知道,比起傍晚,只是观察秃鹰和乌鸦的升起,比起这微不足道的雨丝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被记述。这乱石累累的不毛之地就在那儿,这马匹它将躺在深渊般的,生机勃勃的蓝色大海下边。我了解这逼近的死神,正如我了解既是万物,也是乌有的帝王一样。这秃鹫与乌鸦,还将在它们天生的黑影里飘摇——完美,流畅,高高爬升在略带忧郁的云朵的岩层之上,无需谁宽恕谁。这没用。从死亡到死亡,真实的灵*永远在飘升。很多年过去回过头再看,马的尸骸,那精妙的现代雕塑,苍白,在停滞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学——思考是痛苦的,这就像我在雨中散步,当风正吹过来,雨似乎越下越大。在雨中,我将看见藤蔓上长出心形的绿叶,每片叶子,柔软如天鹅绒,那些细碎的小白花,很抱歉,在祈祷中我还要给它们以祝福,因为它自然、正确,必将出现在我灵*里的神之神祇,它就是存在,就是一切,日光闪耀的河岸上,我能想起的一朵小白花,就这样被遗弃又遭否定?——.2
孟江海,年生于陕西华阴。陕西省作协会员。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高研班学员。著有诗集《另外一个自己》《我是我愤怒的闪电和西风》,散文集《崖畔上的柿子树》。曾任华阴市作协主席、华山诗词学会会长。散文集《崖畔上的柿子树》荣获第四届“杜鹏程文学奖”。孟江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