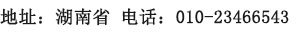刈麦时节刚过,路边的地里飘荡着鲜麦茬的清香气息,加之霏霏阴雨的湿润,整个田野像是一块刚刚出锅的炊饼,温热而不至于那么太烫、婉约而不至于那么直白、馥郁而不至于那么浓烈,一切恰恰刚刚好的感觉,仿佛你想要的都触手可及,你所腹诽的都远在视界之外。
是的,就是在这么个刚刚好的时间和地点,遇见了《诗经》里“薄采”的水芹。水芹是属于伞形科、水芹菜属的一种多年水生宿根草本植物,有水英、牛草、楚葵、刀芹、蜀芹等许多俗称,但在沂水提起这些“舶来品”的名字恐怕没多少人知道。
这是在水牛村东一道婉约的细水河畔,它就是有着典雅名字“秀珍河”的一脉支流。水牛村在杨庄西北11华里处,地处丘陵,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此居住。因临河以前的富户养水牛很多,故以水牛为村名,这也算是个漫漫历史感的村落了,再有这么一泓水潆绕而过,更是将诗经的意蕴从古潺然流带至今。而萌生于斯的水芹,自然就披拂了千年的幽幽古风了。
据统计,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《诗经》三百多篇诗歌中,提到植物一百五十多种,其中有荇菜、葑菲、蒌蒿、苦菜、蕨菜、薇菜、韭菜、荠菜、莼菜等许多家养园子菜,以及水养坡长得野生菜。而以水芹起兴的,除了“泮水”中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”外,还有“采菽”一文的“觱沸槛泉,言采其芹”。
日本江户时代冈元凤编写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中,为芹标注:“水草可食”。或许生活在诗歌之外的劳苦先民已将水芹作为馑食,以佐每天之餐了。
而诗歌中,在泉水汩汩的河畔薄采其芹的劳动人民,是衬托升平世界背景上的一个画面,在被刻意打扮的历史舞台上,王侯将相粉墨亮相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朝代轮流更迭中, 不变的是水芹被吃千年,即便没人再采食的时候,它们依然成丛聚簇娉婷水湄,将一掬野味的清香亘古流传。
或许正在细雨中兀自采撷水芹的大姐,并不知道这些,她只关心多采一些水中那又嫩又绿的芹菜,回去做一顿好饭以飨家人的口吻。流滑丰腴的河水舔舐着岸边葱茏的水草,她所需要的植物就杂生其间。
沉稳善良的大姐忍不住心中洋溢的乐意,一捧水芹抱在怀里,她还惦顾着更远更嫩的一握。水芹菜采回家洗净,可以切段清炒、焯水蒜泥凉拌、老一些的可以剁碎馇豆沫、腌咸菜,这都是沂蒙山人对水芹比较粗粝的烹饪方法,也许是对上世纪中叶岁荒时“忆苦思甜”吃法的延续,正如朱翌诗中所言“幽人本无肉食原,岸草溪毛躬自荐。并堤有芹秀晚春,采掇归来待朝膳。”惟其如此,明人朱橚王将其收录入《救荒本草》水斳以志。
除了诗经于水芹的滥觞,历朝各代也不乏对水芹的咏吟。唐有“芹根生叶石池浅,桐树落花金井香。”明有“翠香芹菜缘沙出,雪色鲥鱼上水来。”;写吃法的有“涧蔬煮蒿芹,水果剥菱芡”“鲜鲫银丝脍,香芹碧涧羹。”所谓“香芹碧涧羹”,在《山家清供》中介绍的做法是“洗浄,入汤焯过,取出,以苦酒研芝蔴,入盐少许,与茴香渍之,可作葅。惟瀹而羹之者,既清而馨,犹碧涧然。”,然而在沂沭河主脉支流间聚水而居的人们,恐怕更多的是会用水芹叶做一锅谷轧汤或者菜糊涂吧,吃一顿煎饼喝一碗这样的浓羹“灌灌缝”,就足可以让人鼓腹而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