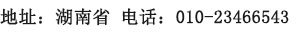颠覆认知:米芾的紫金砚到底是怎么来的?苏东坡借了不还却要陪葬另有隐情?
作者:长盘知·紫金李
砚友们好,我是人称“琅琊砚痴紫金李”的长盘知,最近研究读《米芾传》,又想起元大都出土的那方琅琊紫金砚。
关于琅琊紫金砚,迷雾团团,关于苏东坡借了紫金砚要给自己陪葬的历史公案也是扑所迷离。
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?今天,我通过一系列蛛丝马迹,按照逻辑分析,给大家揭开一角,但这一角足以颠覆大家的认知!
(1)从《紫金研帖》说起
米芾写过一幅字,叫《紫金研贴》(如上图)。
《紫金研帖》为米芾于靖国元年()以后所作。
此帖是米芾追回苏轼所借紫金研的说明,米芾极爱砚台,故不舍给予苏轼陪葬。
释文: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。嘱其子入棺。吾今得之。不以敛。传世之物。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。
苏东坡有那么豪横吗?竟然要拿了米芾的紫金砚陪葬。
(2)米芾的紫金砚怎么来的
米芾的紫金是哪里来的呢?
他自己没说,好像故意隐藏。
南宋初,绍兴府有位老者回忆说:“右*之后,持一风字砚,大尺余,色正赤,用之不减端石,云右*所用者。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。”石扬休是宋仁宗时人,以20贯买了据说是王羲之用过的风字砚。——《砚谱》
这方砚去了哪里?二万买的,不会随意处置吧?
宋代朱长文《墨池篇》引唐询《砚录》:“至和二年,为右史会稽史。自云王右*之后,持一风字砚示予。大且尺余,石色正赤,其理亦细,用之不减端石。”
至和二年是公元,这一年唐询买到了一方右*后人(笔者注: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第七世孙,书法超群。此人是否为智永之后?)的紫石砚。米芾著的《书史》:“有右*古凤池紫石砚,苏子瞻以四十千置。往矣古砚心凹……”
可见苏轼也买过一方右*的紫色砚台。
问题来了:
1.请问,唐询的右*砚哪里去了?
2.请问,苏子瞻花了四十千(可算巨资)买的右*古风池紫石砚哪里去了?他死的时候,为啥不用自己的右*砚陪葬,却要用米芾的紫金砚陪葬?
米芾自己在《宝晋英光集》中提到:“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,与余家所收右*砚无异, 品也。端、歙皆出其下。新得右*紫金砚石,力疾书数日也,吾不来斯不复用此石矣。”
这里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:
3.米芾所藏的右*砚哪里来的?
我认为,石扬休、唐询的右*砚、苏轼的右*古凤池紫石砚、米芾的右*琅琊紫金砚,是同一块,而这块紫金砚,就是元大都出土的那方米芾款琅琊紫金砚!如下图:
钱毛毛先生在《他是宋代书法大家,因个性癫狂而著称,为得到名家书画不择手段》里讲了米芾的两个小故事:
1.米芾在长沙为官之时,得知湘江附近的一座寺庙里,珍藏有一幅唐代书法名家的作品名曰《道林诗》,于是米芾便前去借来欣赏。米芾爱不释手,到了夜里索性直接拿着这幅作品逃之夭夭。无可奈何之下,僧人只能报官,这才夺回宝物。
2.某日,米芾和一个朋友坐船游玩,那个朋友很快就拿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《望略帖》,米芾一见倾心。于是,米芾马上表示想用自己收藏的作品交换,那个朋友似乎不太愿意。米芾急了,竟然说如果不答应自己就要跳河,说着他还马上做出准备跳河的动作来。那个朋友被逼无奈,只得答应和米芾交换。
由此可见,米芾为了得到喜欢的东西,会用一些损招。
所以,极有可能,苏轼的那方右*砚卖给或者送给了米芾,再或者米芾用一些小伎俩把苏轼的右*砚搞到手了。
后来苏东坡病重,想那块砚台了,所以又找米芾借回来, 决定不给米芾了,死要带走!
这就说得通了,不然苏东坡也太豪横了,哪有借了人家的宝物不还回去还要用来给自己陪葬的?
不然的话,苏东坡的右*砚哪里去了?米芾为啥不讲苏东坡右*砚的去向?为啥也不讲自己的右*砚的来历?可见只有一块紫金砚!
后来米芾到琅琊临沂找到了紫金石,于是又制作了一块紫金砚,所以才说“我不来临沂这个地方,结果就是不会有人再恢复使用这种紫金石了”。
(3)元大都出土紫金砚的砚铭之谜
现存世的两方紫金砚应是唐宋遗物。
一方凤字形砚是年上半年出土于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。砚长22.7、宽17.5、厚3.9厘米。砚的前部有两足,砚池向后倾斜,砚面有明显的墨痕。其色正紫,有隐约青花和豆绿色小点,映日遍体泛银星,果然是芒润清响,不同凡品。出土时已残破,右上角砚池部分缺失。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,字有残缺,曰:“此琅琊紫金石所制,易得墨,在诸石之上□永□□□,皆以为端,非也。”落款为“元章”二字。
但是笔者看了下拓片,砚铭并没有“制、之上、非也”等字。如下图:
还有的说,铭文应该是:‘此琅琊紫金石,所囨易得,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,皆以为端囗也。
有研究者则给补上了残缺的几个,成为:“此琅琊紫金石,所镌颇易得墨,在诸石之上,自永徽始制砚,皆以为端,实误也。元章”
断句都不对,更不要说补字!
铭文拓片,我画了下,后面的每行的开头应该跟 行的“此”字对齐
如果按照某些专家考证,内容为:“此琅琊紫金石,所囨易得,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,皆以为端囗也。元章。”或者“此琅琊紫金石所镌,彼易得墨,在诸石之上,自永徽始制砚,然皆以为端,实误也。元章。”那么,如上图,每行的字就参差不齐了!
米芾会这样写吗?没道理!
受南宫砚友鲁之研老师启发,我认为内容应该是:“此琅琊紫金石所制,易得墨在诸石上,乃智永之物(或者传),皆以为端,非也。元章。”如上图。
补全后理应如上图。
理由一:此处似乎是个日字,为智的下一部分
理由二:此处为“製” 一笔。
理由三:此处似乎为“之”字末笔。
南宋初,绍兴府有位老者回忆说:“右*之后,持一风字砚,大尺余,色正赤,用之不减端石,云右*所用者。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。”石扬休是宋仁宗时人,以20贯买了据说是王羲之用过的风字砚。——《砚谱》
右*之后是谁?
智永和尚(生卒年不详),南朝、隋朝人,本名王法极,字智永,会稽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书圣王羲之七世孙,第五子王徽之后代,号"永禅师"。
那么宋朝的王羲之后人,也应该是智永的后人吧?
以上铭文有待商榷,请方家指正。
米芾有三方紫金砚?他到王羲之故乡干了一件神秘事儿……
——感谢米芾,因为他“旧时王谢桌前砚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
原创作者:鲁之揅
有一次,在沂是砚社我跟一个朋友聊琅琊紫金砚。
他说,你不要跟我提紫金砚,紫金砚争议很大,根本搞不清。
我说你错了,紫金砚有争议,但是我说的是琅琊紫金砚,琅琊紫金砚没有争议,它就是琅琊临沂这个地方出的。
确实,紫金砚有很多种,有临朐紫金砚、寿春紫金砚、琅琊紫金砚等,并且它们都有历史记载。但是谁又规定了紫金砚只能有一种、只属于一个地方呢?应该搁置争议、共同开发。
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琅琊紫金砚。
对,琅琊紫金砚,被米芾称赞为“在诸石之上”“皆以为端”的琅琊紫金砚。
(1)初得琅琊紫金砚?
故事还要从米芾索砚说起。
话说*和年间,宋徽宗与蔡京商议,让米芾书写一个大屏风。米芾索要笔砚,徽宗指着御案上的一方砚让他使用。书写完毕,米芾捧砚跪请说:“此砚曾经赐臣濡染,不堪再让陛下使用,请陛下定夺。”宋徽宗大笑,将砚赏给了他。米芾大喜过望,抱砚趋出,墨汁洒污了衣袖。宋徽宗指着他的背影对蔡京说:“人们称他米颠,真是名不虛传!”
此砚为何砚?有人说是端砚,我觉得可能是紫金砚,不然何以令米芾如此痴狂?
但是不管是不是紫金砚,米芾爱砚可见一斑,这奠定了他痴迷寻找紫金砚的基础。
(2)再得琅琊紫金砚?
南宋初,绍兴府有位老者回忆说:“右*之后,持一风字砚,大尺余,色正赤,用之不减端石,云右*所用者。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。”石扬休是宋仁宗时人,以20贯买了据说是王羲之用过的风字砚。——《砚谱》
这方砚去了哪里?二万买的,不会随意处置吧?
米芾著的《书史》:“有右*古凤池紫石砚,苏子瞻以四十千置。往矣古砚心凹……”
可见苏轼也买过一方右*的紫色砚台。
但是苏轼的紫金哪里去了呢?
我认为是送给米芾了,或者被米芾用小伎俩搞走了。
在他自己撰写的《宝晋英光集》里说:“吾年老才得紫金石,与余家所收右*砚无异, 品也,端、歙皆下”。
“余家收右*砚”,是哪里收来的?苏轼的那方还能到了外人之手?
(3)琅琊紫金砚失而复得
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北归途中,当时苏轼已经66岁了,在那时已属高龄;况且又是从瘴疠之地的海南回来,其身早已染上瘴*;加上一年以来旅途劳碌、作息不稳,终于一病不起。
苏轼病重的时候,找米芾借了紫金砚,嘱咐其子要将米芾的紫金砚陪葬。
米芾知道后抢了回来!
后来米芾写了《紫金妍贴》记述此事:“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,嘱其子入棺。吾今得之,不以敛。传世之物,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。”
大意是:之前苏子瞻(苏东坡)从我这里借走了紫金砚台,并且嘱咐他的儿子,等他去世后要将这紫金砚,当做陪葬品一起入殓。现在我拿回了紫金砚,不想让它来当陪葬品。因为一件流传给后世子孙的物品,怎么能够可以与人的遗体这种已经完全涅槃、修成正果的圣洁之物放在一块呢?
苏轼,不至于借人家的宝贝给自己陪葬吧?这里再一次印证,米芾的紫金砚可能就是苏轼的,后来到了米芾手里,临死前苏轼想再要回来陪葬,米芾不肯。
(4)寻找琅琊紫金石
虽然有了右*的琅琊紫金砚,但是,米芾对琅琊紫金石还是念念不忘。
晚年的米芾居住在江淮一带,离琅琊临沂不远。
后来他写了《临沂使君帖》,又称《戎薛帖》。
我们看,全文为spandata-raw-text="""=""data-textnode-index-4="55"data-index-4=""class="character""芾顿首。戎帖一、薛帖五上纳。阴郁。为况如何。芾顿首。临沂使君麾下。spandata-raw-text="""=""data-textnode-index-4="55"data-index-4=""class="character""(此纸本,纵31.4厘米,横25.1厘米,此帖头二行以行书写出,将要言之事交待清楚,至第三行spandata-raw-text="""=""data-textnode-index-4="55"data-index-4=""class="character""如何spandata-raw-text="""=""data-textnode-index-4="55"data-index-4=""class="character""开始变为草书,连绵而下。第四行为受信札者,故空约一行位置,此虽为格式如此,客观上却形成了丰富多变的章法。)
你看看,他开始给临沂的地方官写信了!要搞事?
到底是啥事?没说清楚,“上纳”,相当说见附件。
但是后来,他又写了《*事帖》,这是个好习惯,如下:
内容是:
芾顿首再拜。春和,*事之暇,起居何如?芾幸安。春入沂水,想多临览之乐。只尺何时从公游?临风引向。谨专人奉状,不宣。芾顿首再拜。知府大人麾下。
米芾绍圣四年二月知涟水,闰二月犹在京,则「春和」或须至翌年矣。涟水去沂州不远,自可言「只(通咫)尺」。
意思很明白,春天来了,沂水很美,我能和你一起去游玩吗?
那么临沂使君答应了吗?米芾去临沂去成了吗?
答案就藏在另一副字帖里,如下图:
这是米芾行书《乡石帖》,亦名《紫金帖》,是米芾50岁的一则随笔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米芾在此帖中说:“新得紫金右*乡石,力疾书数日也。吾不来,果不复用此石矣!”
啥意思?意思是说:最近去琅琊临沂,新得到右*王羲之家乡的石头紫金石,滋的不行了,兴奋地用它研墨书写好几天啦!我不来临沂,结果就是没有人重复使用这种石头喽!
结合上文“吾年老才得紫金石,与余家所收右*砚无异, 品也,端、歙皆下”可以知道,米芾去了临沂,并且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紫金石。
(5)琅琊紫金石的开发和普及
近年来,临沂砚界人士越来越重视琅琊紫金砚的开发和制作。很多人加入到了寻找琅琊紫金石的队伍中,到目前,临沂境内紫金砚坑口多达十几个,紫金石品种多达二十多个,品质良莠不齐,有的下发确实在端歙之上,有的只能沦为石雕工艺品。
研究紫金砚颇有成就的当属李淑彬、孙建*、齐石明和李冠增几位先生以及我的学生长盘知等。笔者虽然也研究紫金砚,但是尚属于皮毛阶段。
李淑彬先生最早开展地质探勘,围绕红埠寺进行了调研,后来发现多个坑口,并著有《紫金石的发现和研究》一书。
孙建*先生是《琅琊紫金砚》一书的作者,斋号“紫金石舍”,他从历史考据的角度对右*乡附近的琅琊紫金砚进行了开发,作品得到了砚界知名人士的认可。
齐石明先生,莱芜人士,定居临沂,山东工艺美术大师,擅长制砚和雕刻,在紫金砚制作方面有丰富经验。
李冠增先生,号“紫石山人”,是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先生的学生,擅长文人砚制作和砚铭刊刻,其堂号“紫金阁”,在紫石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。
长盘知,是我的一个小兄弟,人送外号“紫金李”,我于他算是亦师亦友,原名李孩,隐居大宗山,爱好奇石,广泛收集临沂境内砚石,尤其以紫石和紫金石居多,其专著《沂州紫石录》正在创作中。
另外,从网络资料来看,伯多晨、刘祥生、刘祥伦、郭秀江、郭伟、易水寒、闻德莲、张丽萍、张绍云、冯超、曹良铭等人也在紫金石的开发和宣传上有不同贡献,并且各有主张。
我们要感谢米芾,他的执着,他留下的宝贵文字和蛛丝马迹,让我们对琅琊紫金砚有了更多的认识,让我们念念不忘、终有回响,从而在众人的努力下实现了“旧时王谢桌前砚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以至于在淘宝、闲鱼、转转和孔夫子旧书网等上面都能看到琅琊紫金砚的踪影。
琅琊紫金砚,这一王羲之家乡的砚,王羲之用过的砚,难道不应该是每个书法朝圣者营造仪式感的上品吗?一千多年过去了,王羲之用过的纸我们找不到的,他用的毛笔我们也看不到了,甚至他执笔的方式我们都搞不清楚,但是唯有他用过的琅琊紫金砚,幸而重见天日。
前几年有报道称发现了一方王羲之用过的凤池端砚,从而推断端砚开发提前了三百年。我想这里可能有误会,东晋时候广东还属于蛮荒之地,人口稀少、文化落后,端砚的发掘和开采是不大可能的,倒是有可能王羲之的这方“端砚”就是琅琊紫金砚,毕竟琅琊紫金砚和端砚很像以致于“皆以为端也”。
如果我们再开个脑洞,说不定王羲之以后的人到了广东端州这个地方,发现有一种石头很像王羲之紫金砚的石料,所以才决定开采这种石头制作砚台,从而出现了端砚。那就成了先有琅琊紫金砚、后有肇庆端溪砚,或许制作端砚的师傅们听了要受不了了,但是这种推测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
(6)一件小事
年夏的一个下午,天青色等烟雨。有位年轻人带着一方木盒寻访到苏轼墓,他站在碑前,仿佛要与这位心中的超级偶像对话。
他就一直站在那里,等夜幕降临。
在确定四周无人后,他开始掘土,直到他觉得洞足够大了才停下,并把那个木盒放了进去——上面用苏体写着五个字:琅琊紫金砚。下面还有“长盘知”三个小字。
“东坡先生,你要的陪葬品,到货了”。说完这句话,年轻人就消失在夜色里了。
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
或许除了苏东坡……
作者简介:鲁之研(又作“揅”),号揅者,琅琊临沂人,现隐居成都,为砚台收藏家、鉴赏家、设计师。其爱砚,新老不弃、古今兼收,尤嗜紫金砚,常以“南宫砚友”自称;每得一砚,则为之刻铭、题款、拓像,大有乾隆于书画上疯狂盖戳之势,乃获称“砚铭狂魔”,简称“铭魔”。建玩味山房,辟一室曰“不器斋”,数十年已蓄砚三千之多,且立志余生刻砚铭过万。亦寻石制砚,今著有《寻砚记》《藏砚记》《刻砚记》三则。沟通i(鲁之揅助理阿紫)。
附:鲁之揅老师作品
(原创文章,首发于